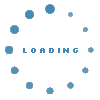看到了媒體關心的報導後,星卉也留下了這樣的留言:午夜夢迴的心裡話意外上了新聞⋯看到這麼多給我鼓勵和加油的朋友們心中的感動、自然不在話下⋯謝謝你們大家的關心與祝福也謝謝這兩報的記者讓我有機會與這麼多人分享我對奶奶的愛⋯至於復出因為經紀約和電視台的合約早已到期這段期間非常感謝他們的體諒給我空間和時間來沉澱心情⋯對於自己未來進一步的規劃尚無確切的想法但我會好好思考的⋯再次感謝大家給我的溫暖我會努力讓自己很好的~希望她能早日走出喪親痛!讓我們重新看到她出現螢光幕前!失去親人真的很痛,星卉加油!請在這裡留言鼓勵她!小編已經將此篇文章轉貼給星卉看了!相信她會看到您們的關心的!二年沒看到她了…希望她能早日重回螢光幕前!!
如何走出痛失親人的悲傷女兒被嬰兒猝死症奪取生命的六個月後,瑪麗(Mary)找到了我。
那時,她已經聘請並解僱了兩名心理醫師,她努力想要從悲傷中恢復過來。
瑪麗是成功的會計師,充滿鬥誌,很少被悲傷壓垮。
她也非常清楚所謂的悲傷的各個階段:否認、憤怒、協商、沮喪和接受。
對於她和我們文化中的許多其他人來說,那意味著悲傷是暫時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預測的,即使是她的生命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損失。
她期待著能放下痛苦,繼續自己的生活。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從表面上看,這些她都已經做到了。
她戴著一張精心構造的面具來面對世界,掩飾的效果相當不錯。
她似乎就是許多人所說的「很堅強」的典範,意思是雖然經歷了打擊,但看起來已經不再悲傷。
在女兒夭折的幾天之後,她就回來繼續工作,言行舉止基本上和以前一樣。
她在生活中的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寶寶去世的六個月之後,她仍然處於深深的絕望之中。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為了在同事、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現得更堅強,她已經疲憊不堪。
就像多數情況一樣,她已經察覺自己「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悲傷,認為頑固的抑鬱正在阻止自己實現接受和解脫。
她想,自己是不是還處在否認的階段。
她還琢磨,自己是否合理地發洩了憤怒。
但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抑鬱了,一位精神科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鬱藥。
她想讓我幫她治療的,也是抑鬱。
倘若是在我行醫的初期,我會把所有精力放在她的抑鬱症上。
她有家族病史嗎?她以前抑鬱過嗎?那些藥管用嗎?她有哪些具體症狀?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會解釋她的狀況。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或者,我會評估她經歷的悲傷的每一個階段,就像她所做的那樣,找出哪個階段還沒有完成。
不過,當瑪麗前來就診時,我已經不那麼做了。
那時距離我自己遭受同樣的打擊,已經過去10年了。
我的第一個孩子不到1歲就去世了。
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瑪麗找到了我。
在我們的第一次治療中,我把瑪麗的抑鬱放在了一邊。
讓她對我講講她女兒的事,而不是描述自己悲傷的症狀。
儘管一開始她有些抗拒,最終還是講了起來。
就像瑪麗人生中的其他許多事項一樣,這個被取名斯蒂芬妮(Stephanie)的寶寶也是按計畫降生的。
瑪麗懷上她非常開心,對這個女兒有很多美好的期盼。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順產後的頭三個月,瑪麗待在家裡照顧斯蒂芬妮。
重返工作很痛苦,瑪麗把帶孩子的事安排得很好,努力平衡著母親的角色和繁忙的工作。
然後,瑪麗給我講述了那個星期六,當她回到家想要看看正在睡覺的女兒時,卻發現斯蒂芬妮沒有任何氣息。
她開始做心肺復甦,丈夫撥打了911。
她和丈夫試圖挽救孩子的時候,做到了異乎尋常的專注。
然後,這個習慣了把所有事情納入掌控之中的女子,不得不把女兒交給了急救人員。
丈夫開車帶著她,跟隨救護車駛向了醫院。
她詳細地描述了等候室的樣子,甚至包括桌椅顏色這樣的細節。
當醫院牧師和醫生一起走進來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孩子已經不在了。
她和丈夫被帶到了一個房間,最後一次把女兒抱在懷裡。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講到這裡,她終於哭了出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她似乎對這種排山倒海的情緒感到不可思議。
這是孩子去世以來,她第一次以這種方式宣洩悲傷。
她說,她從來沒有這樣完整地講述過女兒從孕育到去世的過程。
「我這是怎麼了?」她哭著問。
「都已經過去將近七個月了。
」我非常輕柔地,用簡單的非醫學詞彙告訴瑪麗,她沒事。
她既沒有抑鬱,也沒有陷入悲傷無法自拔,更沒有做錯什麼。
她只是非常傷心,內心被悲傷填滿,不是因為她承受悲傷的方式有什麼不對。
她的悲傷之深,只不過是因為她愛女兒之切。
她聽到這裡時,轉變發生了。
她仍然在哭泣,但面部的肌肉鬆弛了。
我看到她壓抑了數月的情緒釋放了出來。
在這之前,她用大部分精力想要弄清楚自己為什麼無法擺脫悲傷。
她把自己的感受埋在心裡,發誓要堅強起來,因為人理當如此。
現在,在我的辦公室裡,悲傷的各個階段、自我診斷,以及社會的期待都不重要了。
她可以自由地屈服於悲傷。
她和幼小的女兒之間那段深刻的聯繫被重新點燃。
她所承受的打擊成了她的一段故事,一個可以講述和珍藏的故事,而不是一段努力想要遺忘的苦痛經歷。
在我的兒子夭折後,我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那是我當上醫生的第二年,之後就有很多悲痛的患者被介紹到我這裡。
一開始的問題是,我的治療方法對病人和我都沒有幫助。
在上世紀70年代,我接受培訓的時候,悲傷的五個階段是評估一位患者治療進展的指標。
這個模式仍然深刻而頑固地存在於我們的文化意識和心理話語中。
它讓痛苦的人們做出了許多自我診斷和自我批評。
推波助瀾的,則是周圍的人常常含蓄和善意的看法。
一個人的悲傷的時間和強度,都應當適度。
當然,有些來找我尋求幫助的人顯示出了嚴重的、可以診斷的症狀,這些症狀需要治療。
然而許多人尋求幫助只是因為他們和周圍的人認為,他們悲傷的時間該結束了。
實際上,悲傷就像指紋一樣獨一無二,它不會遵照任何時間安排或者社會期待。
根據我自己和我的患者的經歷,我現在想說,失去至親的故事有三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與依戀程度有關:指的是你和去世者之間的關係。
理解感情程度和悲傷程度的關係,會讓多數患者感到極大的寬慰。
我常常告訴他們,悲傷的強度和愛的深度是相稱的。
第二個章節是死亡本身。
在這個階段,失去至親的人常常會開始質疑自己的精神狀況,如果是過早死亡或創傷性的死亡,就尤其如此。
瑪麗對自己在艱難時期把控全局的能力感到自豪。
她女兒的死亡導致的深度情緒混亂讓她抓狂。
她會儘可能地抵製這種抓狂的狀態,抑製自然產生的痛苦和折磨。
第三個章節是從外部世界不再陪你一同悲傷的時候開始的,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瑪麗想要讓家人、朋友和自己相信,她很快會從悲傷中走出來。
這個過程讓人精疲力盡。
她真正需要的是讓自己沉浸在悲傷裡,然後接受它。
我建議成立一個互助組,被瑪麗拒絕了。
但是我堅持這麼做。
她後來描述了在其他失去子女的父母面前感受到的放鬆,在這群人中,自己再也不需要掩飾什麼。
在那裡,人們懂得,自己根本不想得到解脫。
解脫就意味著割捨掉一段神聖的感情。
「所有的痛苦經歷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你把它放進一個故事裡,或者講述一個關於它的故事,」作家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說。
當失去成了一個故事,悲傷的方式就沒有對錯之分。
人們就無需感到回歸正常生活的壓力。
激烈或長期的痛苦都不丟人。
悲傷、悔恨、疑惑、渴望,以及所有痛苦的經歷,都成為關於那位逝者的愛的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