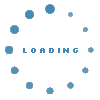我並不清楚,祖母從什麼時候開始討厭我的。
奇怪的是我卻把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銘記於心,如今還要拿出來念叨。
二十多年前,祖母六十歲,她帶著我和叔叔家的弟弟一起去公園劃船。
如今想起來,祖母很會打扮,沒有選擇改革開放初期的奼紫嫣紅,反而是穿著墨綠色的裙子,再搭配一件月牙白的女式襯衫。高高瘦瘦的她,走起路來稱得上搖曳。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然而,搖曳的老祖母不知道什麼原因地發起了脾氣。她氣憤地對我說,「你這麼不聽話,自己在這裡玩吧!」說完,她牽著弟弟的手,走出了公園。
我想祖母和弟弟應該是坐著老式的有軌電車回家了。
我沒哭,也沒害怕,一個人蹲在公園的人工湖邊,看著暗色的水以不被人察覺的速度流動,看著偶爾浮上水麵吐泡泡的小魚。
然後,天就黑了。
等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在泣不成聲的母親的懷抱裏。
據說,父母急三火四、大喊大叫地衝進公園時,我已經在湖邊的長椅上睡著了。
在這件事不久之後,母親就帶著我搬出了祖母的老房子。
母親和父親分居了快一年,父親才從祖母的老房子裡搬出來。
母親從此之後對我一直很寬容。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我把留了六七年的長髮剪成板寸,像個假小子一樣,和一群男生打籃球。別人都說「這樣早晚會出事」,母親特別淡定地笑笑。
結果,我既沒早戀也沒早孕,反而是那些看起來乖巧的女生,動不動就爆出早戀、成績下滑的老套故事。
我考上了醫科大學,學臨床醫學。畢業之前,母親問我,「要不要送禮,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我想了好幾天,才對母親說,「媽,你拿送禮的錢養我兩年不工作,行不行?」父親氣得在一旁要打我。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母親攔住他,對我說,「行。」
說完這個「行」字還沒到一周,祖母就打電話過來,「二十多歲的大姑娘,不工作,家裡街上的晃悠,早晚要出事……」母親不等祖母說完,「啪」一聲,乾脆利落地掛了電話。
別看母親敢直截了當地掛祖母的電話,可是逢年過節的時候,父親依舊帶著我們一家三口到祖母的老房子去團圓。
祖母現在和叔叔一起生活。叔叔得意得不得了。我心想,「看他那搖頭晃尾巴的樣子,不過就是因為可以得到祖母的老房子罷了。」
說是祖母的老房子,也不盡然。祖父雖然是入贅到祖母家,但這老房子怎麼說也有祖父的一部分。
可惜,祖父這個人不善言辭,性格又懦弱,全家上下自然全都要聽祖母這位老祖宗的了。
大學畢業這兩年,我花了家裡不少錢,到處玩,國內差不多跑遍了,又去了一趟歐洲、一趟美國。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後來我想去澳洲的時候,父親說,「有本事自己賺錢去。」
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掐著手指頭算了算,這一算嚇得我一晚上沒睡覺,真是花得錢太多了。每次我管母親要錢的時候,母親問都不問,直接給我。現在想一想,估計父母這輩子攢的錢有一半都被我在這兩年花掉了。
我不想在一個九流的醫院裡當門診小大夫。
人總要活著,活著就需要吃穿拉撒,吃穿拉撒都要錢,所以活著是需要錢的。
我總不能繼續啃老。
我總要幹點什麼。
後來我就想起了半夜喝醉酒的時候,和一群男男女女跑到這個城市的街頭去塗鴉。其中有一個挺高挺胖的男的,據說是開刺青店的。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我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這個男的的電話。
這個男的露在衣服外麵的,除了臉,全都是刺青。他說,「你就叫我老霍吧!」
我開始在老霍的店裡上班。
其實,刺青的人不多也不少,大部分都是在肩膀、肋骨、手臂內側、腳踝……各種不起眼的地方刺一個小小的圖案。
「這些人可真沒勁啊!」我說。
店裡沒有客人,老霍望著窗外發獃。聽到我這麼說,他就問我,「你好歹也是在刺青店裡上班的,你自己都沒刺青,咋好意思告訴客人『刺青一點都不疼』。」一身刺青的老霍學著我的樣子。
想了想,我就同意老霍給我刺青。
「要玩就玩個大的。」我說,「給我刺一條花臂。」
花臂也不是說刺馬上就能刺完的。
而且刺青也實在太疼了。
刺的過程中,一開始我還能感覺到老霍的熱乎乎的呼氣撲在我的手臂上,後來就被針紮得麻木了,啥也感覺不到了。
等我穿著襯衫回家時,眼睛已經哭腫了。整個刺青過程中,我就一直在哭。
是真疼。
母親看我,也沒問什麼,「怎麼回來這麼晚,給你留了飯。」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地過去。
我發現有了工作的好處就是,父親要帶我和母親去祖母家裡的時候,我可以以上班為藉口逃開。
但過年的時候肯定要去見祖母的。
去老房子。
這成了父母和我對去祖母家的一種特定的說法。
後來,「老房子」這三個字逐漸成了祖母的代名詞。
母親會問,「老房子怎麼說?」
父親就會回答,「她說什麼什麼什麼。」
過年的時候,弟弟說要放鞭——就是叔叔家的那個弟弟。我們家人丁實在不興旺。祖母有四個孩子,這四個孩子分別各有一個孩子。除了我,孫輩都是男孩。
於是我就和孫輩的另外三個男的出去放鞭。
我對放鞭這件事沒有絲毫的興趣。
我對弟弟說,「有煙嗎?」
弟弟詫異地瞟了我一眼,掏出煙,遞給我一根。
我從牛仔褲的口袋裡掏出打火機,點燃了,深深地吸了一口。
弟弟一眼就看見我從羽絨服袖口露出來的手腕上,有著鮮艷的刺青。
弟弟開始大呼小叫,另外兩個也跑過來看。
於是,祖母終於知道我在刺青店上班,而且還自甘墮落地紋了一條花臂。
「這個孩子算是被你們毀了!」祖母在除夕的年夜飯上暴跳如雷。
母親一邊嗑瓜子一邊看春晚,偶爾看看那幾位叔叔。
父親勸著祖母。
另外三個叔叔在看熱鬧。
忽然,屋子裡瀰漫著一股臭氣。
大家開始尋找這臭氣的源頭。
叔叔家那個特別賤的弟弟最先發現了,「是爺爺!爺爺拉在褲子裡了!」
祖父還一臉安詳地看著電視。
祖母愣住了。
這個年在除夕夜裡就提前結束了。
祖母要麵對兩件事,一件是我是一個在刺青店上班、紋了一條花臂的「女流氓」;另一件事是祖父癡呆了。
從來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用的我,忽然之間成了焦點。
三個叔叔開始拿我當反麵教材,告訴自己的兒子千萬不要誤入歧途,也千萬不要找一個像我這樣誤入歧途的女的當女朋友。
父親覺得很丟人似的,我覺得可笑。父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在刺青店上班,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刺了一條花臂。
祖母慌了神兒,立刻召集所有的兒子、孫子。大半夜的,召集來的也只有四個兒子,外加我這個「那個刺青店的工作還不如不幹」的「女流氓」、女閒人。別的孫子都是有光明前途的,還是要好好睡覺,以免耽誤了第二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