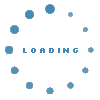|
I like pessimists. They』re always the ones who bring life jackets for the boat.
我喜歡悲觀主義者。總是他們,才是那些帶救生衣上船的人。
- Lisa Kleypas, Christmas Eve at Friday Harbor
又到了高考的季節,這兩天也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高考結束的那天。(並沒有暴露年齡)最後一場考試結束,同學們陷入了狂歡。他們大笑,摔東西,撕課本,通宵唱歌和泡吧。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他們告訴我,美好的人生終於開始了。
但那時的我,卻怎麼也無法產生出像他們那樣,對未來無限憧憬的情緒,反而有種黃金時代結束的漠然。我默默地回家,像往常那樣睡了一覺,心裡想著,在這一天以後的人生,並不會變好吧。
事實上,在整個學習生涯裏,這種情緒一直困擾著我:我總是被班主任、心理輔導老師談話,他們都會問我,你為什麼要這麼悲觀,為什麼不能積極向上一些?對此,我思考了很多年,依然沒有答案。我永遠也無法做到人群中的有些人那樣,看上去每天都充滿希望和「正能量」。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今天的文章,我們也想和你來聊聊悲觀這個主題。在心理學裡,作為一種氣質的悲觀是與生俱來的嗎?樂觀一定是好的,悲觀一定是不好的嗎?作為一個悲觀者,我們可以以何種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
悲觀是什麼?
在維基百科裡,「悲觀」(pessimism)的定義是「一種總是期待不良後果的精神狀態,或者一種相信『在生命中,惡總是勝過善,困苦總是多過享受』的信念」。
在心理學裡,對悲觀的研究幾乎是和對抑鬱的研究同時開始的,在貝克1961年編製的抑鬱量表中,對未來的期待是正麵還是負麵也被作為一個判斷因素。Wellesley College的心理學教授Julie Norem在超過20年的時間裡致力於研究「悲觀」。她認為,在過往的語境中,我們往往將「悲觀」的含義簡化了,但實際上,悲觀含有更豐富的語義,並分為不同的類型。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她列出了悲觀的三種常見類型:
· 氣質性悲觀(dispositional pessimism):我們日常所說的悲觀或樂觀,往往都是基於氣質性層麵的。氣質性悲觀指的是一種整體的傾向性,即人們在對未來的看法上,長期傾向於期待壞的結果。(Rossman, 2010)(在本文後半部分提到的「悲觀」、「樂觀」,如無特殊說明,都指氣質性的悲觀。)
· 歸因性悲觀(attributional pessimism),也被稱為解釋性悲觀(explanatory pessimism),主要強調的是在解釋風格上的悲觀傾向,即在一件事情發生後對它進行解釋時,總會採取內在的、穩定的負麵歸因。與氣質性悲觀不同的是,它強調對過去發生事件的解釋,而不是對未來的期待。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 防禦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除了以上兩種,還有一種悲觀是在認知策略層麵的,即防禦性的悲觀。防禦性悲觀的概念由Nancy Cantor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它指的是人們會在事件發生前,將期待降到比較低的水平,想象出最壞的可能的情境——這看起來讓人擔心,但它卻不是一種消極的自證預言。當一個人在處於防禦性悲觀的情緒裏的時候,他們的情緒是冷靜的,他們知道這只是數種可能性中最壞的一種而已,並不是唯一和註定的結局。這種防禦性悲觀的目的也是為了減少最壞可能發生的概率,以及假如真的發生了最壞的情況,也能更好地麵對和有條不紊地處理。
Julie Norem認為,防禦性悲觀是一種非常有用的降低焦慮的認知策略。
| sponsored ads |
|
|
| sponsored ads |
當人產生焦慮情緒時,假裝樂觀、或者迫使自己往好的方麵想是無濟於事的,防禦性悲觀的策略會使你進入到焦慮的深處,將焦慮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部分,就這些具體的部分來做好充足的準備,避免壞的結果產生。「如果你不自己親身體驗焦慮,就很難洞察在其中讓你感到無助的到底是什麼。」Julie Norem說。
在這裡,需要做一下防禦性悲觀與幾個概念的辨析。
讀過我們往期文章的朋友可能還記得,我們解釋過一個叫做「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心理學現象(回復【自證預言】給公號,查看往期文章),即我們先入為主的判斷(無論正確與否)會影響到我們之後的行為,以至於這個判斷真的實現。當自證預言是消極的,我們甚至可能會主動獲取一個消極的答案,來平衡自己的負麵情緒。
但防禦性悲觀和消極的自證預言有本質的區別。
1. 想象的方式不同:儘管對可能發生的事件都懷有悲觀的想象,防禦性悲觀更多的是懷有對壞的可能性的想象,這種想象是偏細節性的,他們會列出可能發生的情境,將壞的可能細化成一個個事件;而自證預言只是一種籠統的、毀滅性的預測,他們總是使用「永遠」、「絕不會」、「總是」這樣絕對化、概括的詞語,覺得悲劇一定會發生。
2. 懷有悲觀想象後,二者的做法不同:防禦性悲觀的人,會考慮當這些壞事發生後該怎麼辦,能否努力讓壞事不發生。他們也會因為擔憂而做好充足的準備,以避免壞的事情發生,降低焦慮水平;做出消極自證預言的人則不會有所作為,而是放任壞事發生,甚至主動促使壞事發生。
與防禦性悲觀相對的,還有「自我設限」(self-handicapping)的態度和因為不願意麵對失敗結果而導致的「拖延症」。自我設限的人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以給未來可能的失敗找好借口;而做事拖延的人是逃避考慮可能的壞結果,他們應對的方式是不去開始,讓害怕的失敗儘可能來得更晚。防禦性悲觀卻是客觀而勇敢的, 他們客觀地看到可能出現的壞情況,但絕不放棄爭取最好的可能,以及做好準備減少損失。
研究表明,會持有消極的自證預言、自我設限、做事拖延的人,往往自尊水平都比較低,他們會低估自己改變境況的能力;而Norem在2006年的實驗發現,防禦性悲觀的認知策略有助於提高自尊水平。研究者將大學生分成樂觀者和悲觀者兩組,悲觀者中又有一部分人使用防禦性悲觀策略,另一部分人沒有使用。研究者對這些大學生在4年內的變化做了跟蹤,發現4年後,那些樂觀者的自尊水平沒有什麼變化,非防禦性悲觀者的自尊水平還略有下降,只有使用防禦性悲觀策略的人,在入學時自尊水平較低,但畢業時自尊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和樂觀者的自尊水平相當。
悲觀和樂觀各有哪些好處?
在日常語境中,我們常常認為樂觀是有益的,悲觀是有害的。但2011年發表在《社會認知》雜誌上的一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研究者Abigail Hazlett認為,悲觀和樂觀只是我們在麵對人生的不可預測性時,所採取的不同的動機取向,他們沒有好壞之分。
樂觀者的動機取向是「進步」(advancement)取向,人生觀是「進步關注」(promotion focus)的。他們更善於應對積極的反饋,因此總是看到好的可能。
悲觀者的動機取向是「安全」(security)取向,人生觀是「阻礙關注」(preventiontion focus)的。他們在麵對未知時,更想要獲得安全感和確定感,因此總是會去考慮到那些最壞的事情。
Abigail Hazlett認為,違反自己本身的動機取向,一味地要求自己用某種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在變位詞測試的實驗中他發現,當被試採用與自己原本動機取向相同的策略去做測試時,獲得的成績是最好的。悲觀的人採用樂觀的策略,和樂觀的人採用悲觀的策略,都不會有好結果。
一係列研究也表明,樂觀與悲觀各有好處。Julie Norem認為,人們往往高估了樂觀的好處,低估了樂觀的壞處。「長期以來,人們在『必須表現得樂觀』這一點上,承受的壓力太大了,這是比悲觀更有可能帶來負麵影響的事。」
以下是一些關於樂觀和悲觀的研究成果。
· 樂觀的人適合當CEO,悲觀的人可能在金融市場上更加擅長。
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的人容易成功?研究表明,他們擅長的領域可能不太一樣。
2012年,杜克大學的研究對美國企業的1011名CEO和534名CFO做了人格測試,結果顯示,80.2%的CEO是那些「非常樂觀」的人(18分以上),其量表平均分比普通人的平均水平(Scheier etal.1994)高出80%左右;90.2%的CEO具有冒險精神,他們不畏懼即將到來的風險。
相比之下,擔任CFO(首席財務官)職位的人則遠不如CEO那麼樂觀,而且他們自己也這麼覺得:在自我報告中,有94.9%的CFO都認為,他們的CEO比自己更樂觀,而且樂觀不限於商業層麵,而是對生活的方方麵麵。在歐洲、亞洲企業管理者的測試中也得出了相應的結論。
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CEO需要對自己的商業前景持有更強大的信心,並勇於冒險;而CFO則更需要對公司進行風險的把控。
· 樂觀使人健康,但悲觀的老年人可能更長壽。
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有助於健康,這似乎是共識,也被一係列研究反覆證明:樂觀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少患心血管疾病,甚至更少患感冒。
然而,德國學者 Frieder Lang研究認為,樂觀未必在所有情況下都有助於健康。研究基於對4萬多名年齡在18-96歲之間的人的訪談,研究發現,32%過度樂觀的人,殘疾的可能性高出其他人9.5%,死亡風險高於其他人10%。研究者認為,可能是過於樂觀會使他們忽視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險。
· 在親密關係中,樂觀和悲觀都在發揮作用。
在親密關係中,樂觀的伴侶會比較容易獲得幸福嗎?
2010年,田納西大學的James McNulty發表了一係列對新婚夫婦的跟蹤研究,在他們結婚的頭4年裡分別進行8次滿意度調查。他發現,並非是抱有樂觀/悲觀的態度就能對婚姻有好處。
McNulty進行了研究,分析了氣質悲觀和婚姻滿意度的關係。研究針對82對新婚夫婦,分析他們對未來抱有的態度與婚姻滿意度的影響。他將他們分成樂觀組(傾向於對婚姻的未來充滿希望)和悲觀組(傾向於認為未來的婚姻會充滿坎坷)。結果發現,那些持有樂觀期待的伴侶,對婚姻的滿意度顯著逐年下降。悲觀組則不一定。
人生來就悲觀嗎?
基因對氣質性的悲觀/樂觀有很大的決定作用
在探尋抑鬱症與基因的關係同時,神經科學也開始研究悲觀/樂觀的氣質與基因的關係。2007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則研究宣布,有大約32%的人生來就擁有一種叫做ADRA2B-deletion的基因變異體,這使得他們對消極的經歷保持更鮮活、更富含細節的記憶;他們也會更多地放大負麵的經歷和情緒,對人生持更悲觀的態度。
並且,這種趨勢可能是難以改變的。2014年,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研究者宣布,他們首次在神經科學上證明了樂觀者與悲觀者在腦部活動上的確存在區別。他們對被試進行了樂觀與悲觀的測試,然後讓他們針對一些照片中的場景,努力往積極的方麵想,比如在看到一個男人拿刀放在女人的喉嚨上時,想象其結果是女人最終掙脫並逃跑。
在實驗過程中進行腦部掃描的結果顯示,那些悲觀者使自己去想象樂觀的結果時,由於這與他們本來的想法相悖,腦部活動會表現得異常活躍(主要由LPP-late positive potential和SPN- StimulusPreceding Negativity兩項指標得出),這會使他們感受到「矛盾的、事與願違的痛苦」。
環境影響了氣質的形成
Bates基於852對雙胞胎的研究,認為在基因層麵上,氣質性的樂觀與悲觀從一開始就是兩個不同的分支,但最終氣質的形成則是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父母的教育和行為表現、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鄰裏社區的環境等,都是可能影響後天氣質發展的因素。
一個人自身過去的經歷和體驗也會影響樂觀和悲觀的傾向。
針對不同類型的悲觀,Julie Norem分析認為,氣質性的悲觀是與生俱來的,最難以改變;歸因性的悲觀是可以習得和改變的(Seligman, 1991);防禦性的悲觀則是最容易習得的。
Julie Norem說,我們總習慣用一個概念來定義某個人,將樂觀者與悲觀者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但實際上,就如同樂觀與悲觀本身含有豐富的語義與類型一樣,絕對的樂觀者和絕對的悲觀者都是極少數的。大多數人都可能會在某些方麵是樂觀的,在另一些方麵是悲觀的,比如,有的人可能在對待金錢時是一個防禦性的悲觀者,又在社交上是一個策略性的樂觀者。而且,樂觀或悲觀的氣質也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發展,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發生改變。
最後,當我們在談論「悲觀」或者「悲觀主義」時,我們還要區分心理學意義上的悲觀和哲學層麵的悲觀。在哲學層麵上的悲觀不是氣質或情緒上的,而是這樣一種世界觀或價值標準:「力圖勇敢地直麵令人不快的現實世界,消除可能造成不良後果的非理性希望和期待」。(Wikipedia)
在西方哲學中,叔本華被稱作是著名的悲觀主義哲學家,他說「活著就是苦難,生存就是煉獄」,人生就像鐘擺,「搖擺在痛苦和無聊之間」;他還把人生比作一個環形的跑道,上麵布滿了燒得通紅的木炭,僅有幾處納涼之地。有的人會在那幾塊納涼之地陷入樂觀的幻想,但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安慰。
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一種清醒地認識世界之後,仍然能夠勇敢而理性地生活的人生態度。
以上,晚安。
References:
Norem, J. K. (2001). Defensive pessimism,optimism, and pessimism.
Norem, J. (2008). The positive powerof negative thinking. Basic Books.
Norem, J. K., & Andreas Burdzovic, J.A. (2007). Understanding journeys: Individual growth analysis as a tool forstudy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ange over time. Handbook of methodsin positive psychology, 477-486.
Neff, L. A., & Geers, A. L. (2013).Optimistic expectations in early marriage: A resource or vulnerability foradaptive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105(1), 38.
McNulty, J. K. (2010). When positiveprocesses hurt relationship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science, 19(3), 167-171.
Mason J, Hartwig R, Moran T, Jendrusina A,Kross E. Neural markers of positive reappraisal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trait reappraisal and worry. Journal of AbnormalPsychology. 2014.
Vaughan, S. C. (2001). Half empty,half full: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optimism. Harcourt Inc.
Bates, T. C. (2015). The glass is half fulland half empty: A population-representative twin study testing if optimism andpessimism are distinct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psychology, 10(6), 533-542.
|